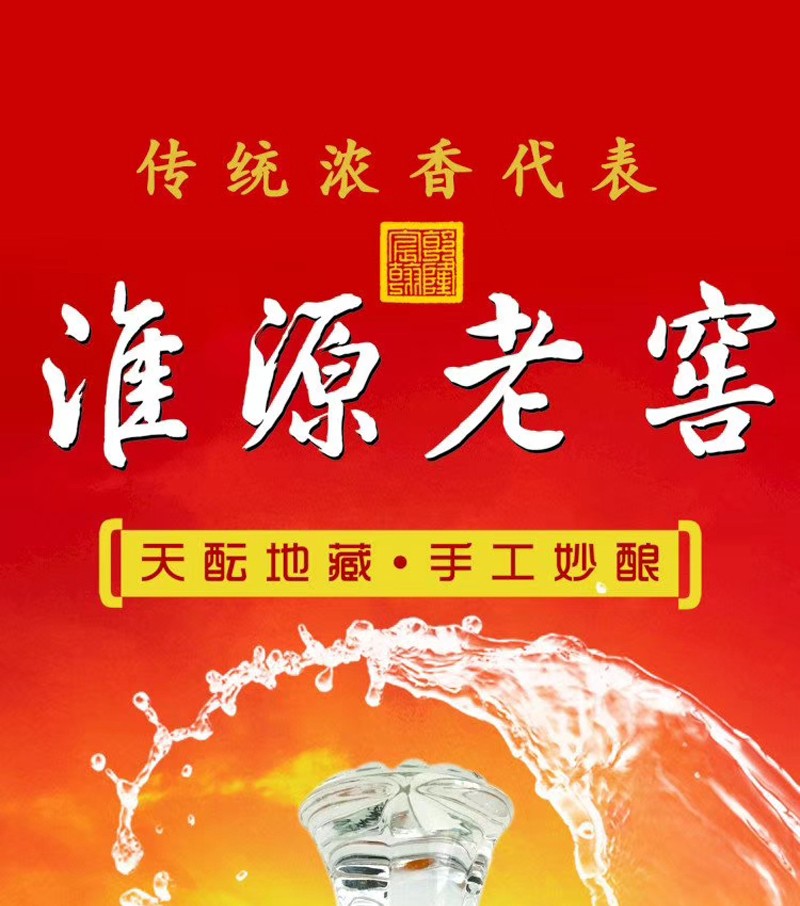太白顶云端那片海
有人说孩子是自己的好,风景是别家的好,但对我而言,外面的风景再好,我只是一个看客。每次出行的时候,总是惦记着家乡的山水,我看青山多娇媚,青山看我不知是否亦如此。问青山 ,青山不语,但丝毫不影响我的爱,我爱桐柏山,我爱淮河源,我深深爱着这片山山水水,爱得情深,爱得真挚。
也许每一个文人,都有着几分偏执和疯狂,特别是对桐柏山的最高峰太白顶,认为自己已到了虔诚和信仰的地步。
人生记忆最深刻的几次徒步壮举,似乎都与太白顶有关,中学时我曾经从崎岖的山路上用了一天的时候去登顶;千禧年元旦的第一场大雪,我曾徒步从水帘寺走到西山门,从早上八点走到下午四点,全程27公里,还踏着齐膝的积雪;我已记不清多少次夜里三点多,为了拍摄日出云海打着手电上山;还有刚刚的那个深夜,狂风大雾,我说想夜游,云居深处的三位朋友,硬是陪我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,甚至平生第一次遇到狐狸先生。
轻车熟路,这个词对我开车跑太白顶这条路再恰切不过。我喜欢在晨曦的早上,畅通无阻地盘旋而上,我喜欢在浓雾的深夜,一个人驾车漂移而下,山上是仙间胜境,山下是人间烟火,而我游离于两者之间。
黄山的云海我看过,因人太多,留下的印象好像是人海中升起了云海;泰山的日出我也看过,因走了一夜的山路,当两万多游客统一穿着租来的军大衣寂寞而壮观坐在泰山顶的时候,有的只是困意累意和芸芸众生的无奈,仙境里不会有这么多的大衣客。
只有太白顶的这片云海,既是伸手可触的,又是可望不可及、可遇不可求的。多年的登山经验,我已经掌握了云海的时间,如果连续下个四五天的小雨,雨后初晴的早晨,云海的机率很大。当然云居的朋友们说,看云海最好就是在太白顶住下来,安心的等,就像看庭前的花开花落,看潮来潮去,去留无意最好。
在淮河之源、太白之巅,雄居着一座庄严的寺院——云台禅寺,是临济宗白云山系的祖庭。白云法脉深厚,高僧辈出,在海内外影响甚广。经过几年的修复与重建,现在的云台禅寺殿堂巍峨,圣像庄严,门坊轩昂,规模宏伟。以前对寺院保持着恭敬,从不轻易进入,尊重他们的信仰,怕扰了他们修行。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,他们在寺院修行,我们在尘世修行,只是环境不同,心境不同而已。
寺院也是有品位的,有文化的寺院,多了几分品味和禅意。特别喜欢寺院大门上登高望远的那几个字,也喜欢侧门上的云起,山上还有两个茶室,一个叫云堂,一个叫云居,单是看这些名字,便看不到云海,也是有云意的,感觉在云端之上。尘世间的茶室,只可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,只可背靠青山,柳暗花明,只有这云堂和云居,安在云端之上,简洁到没有任何装饰和点缀。云起之时,云堂里烧得通红的壁炉,茶炉里煮得沸腾的白茶,是人世间没有的禅意和清欢,是仙境里的人间烟火和灵魂温暖。
云是云,云是白色的,轻盈的;海是海,海是蔚蓝的,深邃的,如果你不曾真正见过太白顶的云海,你就无法理解云海的真正含义。云海之神奇,奇在似海非海,非海似海;云海之神秘,秘在变幻莫测,气象万千。
而太白顶的这片云海,更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,每次我的美图发完朋友圈,就会有许多朋友抱怨着登顶为啥不叫上他们,我笑着说他们是叶公好龙,别说夜里登顶,就是白天,他们也不一定能有这么大的耐心来等待。
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阳光明媚,转瞬间就云雾弥漫,几尺之外便看不见人也看不见山,那铺天盖地的雾却突然散去,云海便呼啸而来,像峰峦,像河流,像雄狮,像奔马……
常常在云海来的时候,我站在空旷的石巅上,叹为观止,任风吹乱我的头发,任云拂乱我的裙裾,任海搅乱我的思绪,竟然常常忘了手中的相机,等回过神来,选好角度拍流云飞渡的延时,那云海说去就去,毫不缠绵和停留。
尘世的一切都不复存在。远山迷离,近谷空蒙,若恰逢红日冉冉,茫茫云海之上便会展现一轮五彩光环,似晕非晕,似虹非虹,一个圆环悬在天幕之中,那光圈无限扩散无限放大,像佛祖再世,神仙显灵,这就是难得一见的“云海佛光”。回望寺院,极其柔和的光笼罩着,山风挟裹着白云,清月还徘徊在上空,幻化出缥缈的世界,仿佛来到蓬莱仙境。
“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”因为难得,所以在意,因为罕见,所以流连,在太白看云海,是稍纵即逝的一种天赐,不仅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,还会给人以捉摸不定与恣意潇洒。
正是云海的瞬息万变,才感觉太白的笃定,山间的一草一木、寺院的一砖一瓦都是笃定的,云来云去,霜来雪往,他们都无声地保持着笃定,无语无声,无去无从,无喜无悲……
泰山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来不看云,而只有看过太白顶的云海之后,山还是山,云还是云,只是那云海,只有那片云海,纯净无比,浩瀚无边,常常在我们寂坐的时候,常常在我们行走的时候,一次次的没过我们的心田,一次次的没过我们的世界。
生于此岸,却喜彼岸花开,生于尘间,却喜云端清凉。酌一片云海禅心,牵一缕梵音佛光,繁华于茶间宁静,沧海于云间桑田,在云端之上,云堂之内,享一段坐禅时光……(文:海容)